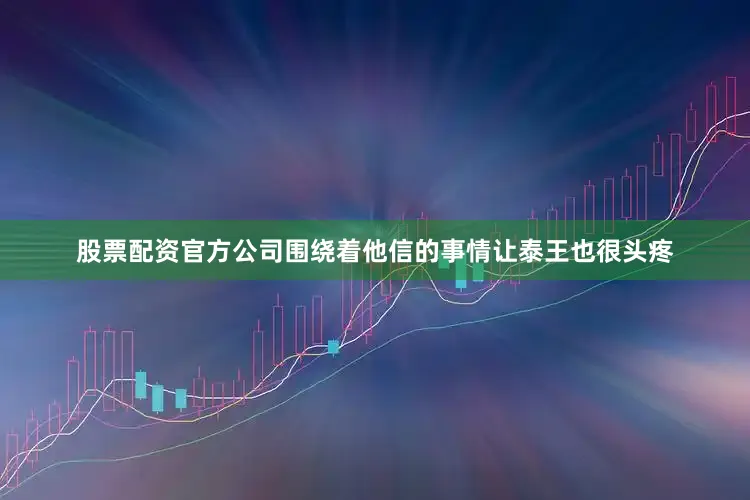我叫王建业,提起1989年那个春天,我这心里头啊,就跟刚出锅的豆浆似的,热乎乎、暖洋洋的。那年我二十岁,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就跟着我爹在村里的砖窑厂干活。每天不是脱坯就是烧窑,累得跟条狗似的,浑身上下除了泥就是汗,活脱脱一个“泥人张”。
我们家住村东头,三间老旧的土坯房,院子不大,就种了棵歪脖子枣树。隔壁那院子,空了好几年了,听说原来的主家搬去了县城。
那年三月,春暖花开的时候,隔壁院子突然热闹了起来。一辆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地开进来,从车上跳下来一对母女。老的看着五十出头,一脸风霜;小的瞧着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,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,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胸前,眼睛又大又亮,就是小脸蜡黄,瘦得跟根豆芽菜似的。
我娘是个热心肠,看她们娘俩搬家辛苦,就端了碗热茶过去。一来二去,就熟络了。
我娘回来跟我说,那姑娘叫李月娥,她爹前年得急病没了,家里欠了一屁股债。她们娘俩在原来的村子待不下去了,就投奔到我们村的远房亲戚家,盘下了这间空院子,准备做点豆腐卖,糊口度日。
我听了,心里就有点犯嘀咕。做豆腐可是个辛苦活,起早贪黑不说,还得有力气推那死沉死沉的石磨。就李月娥那小身板,能行吗?
展开剩余88%第二天,天还没亮,我就被一阵“吱呀呀”的磨盘声给吵醒了。我披上衣裳,悄悄扒着院墙的豁口往隔壁瞅。
只见院子中央,李月娥正费力地推着那盘大石磨。她个子小,力气也小,推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,额头上的汗珠子,在清晨的微光下亮晶晶的。她娘在一旁,一边往磨眼里添泡好的黄豆,一边心疼地给她擦汗。
我看着,心里头莫名地就有点不是滋味。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家,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,却要扛起这么重的担子。
“建业,看啥呢?”我娘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,拍了我一下。
我老脸一红,赶紧站直了身子。
我娘叹了口气:“唉,这娘俩,也是可怜人。你爹说了,以后咱家能帮衬的,就多帮衬点。”
从那天起,我就多了个心眼。每天去砖窑厂上工前,我都会先挑满自家院里的两口大水缸,然后再悄悄地给隔壁李月娥家的水缸也给挑满。她家磨豆腐用水多,光靠她娘俩挑,得跑断腿。
我每次都趁着天黑,干得神不知鬼不觉。可没想到,还是被她给发现了。
那天早上,我刚放下扁担,直起腰捶捶酸痛的后背,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:“是你?”
我一回头,看见李月娥就站在我身后,手里还端着个粗瓷碗,碗里是刚出锅、还冒着热气的豆浆。
我心里一慌,跟做了贼似的,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……我就是看你们家缸里没水了……”
她看着我,那双大眼睛在晨光里亮晶-晶的。她没说谢,也没说别的,只是把手里的碗往前递了递:“喝吧,刚磨的,还热乎。”
我接过碗,那碗还带着她的体温,烫得我手心一颤。我低着头,“咕咚咕咚”就把一碗豆浆喝了个底朝天。那豆浆,磨得又浓又滑,一股子豆香味,直往心里钻,比我娘做的都好喝。
“好喝吗?”她看着我,嘴角挂着一丝浅浅的笑。
我胡乱抹了把嘴,使劲点头:“好喝!”
从那天起,我帮她家挑水,就从偷偷摸摸变成了光明正大。每天早上,我挑完水,她都会给我留一碗热豆浆。我俩就站在院子里,一个喝豆浆,一个看着我喝,谁也不说话,但心里头,都跟明镜似的。
有一天,我去砖窑厂上工,路上碰见村里的二流子王麻子。他斜着眼看我,阴阳怪气地说:“哟,建业,听说你跟隔壁那‘豆腐西施’好上了?啥时候办事啊,也让哥几个喝杯喜酒啊?”
我气得脸都青了,攥着拳头就想揍他。
“咋的?想动手啊?”王麻子往后一跳,贱兮兮地笑,“我就说说,你急啥。不过我可提醒你,那丫头可是个扫把星,克夫!你小子可当心点!”
我再也忍不住了,一拳就揍在了他脸上。我俩就在村口的大路上扭打了起来。我虽然力气大,但他常年打架,下手黑,没几下,我脸上就挂了彩。
就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,一声厉喝传来:“住手!”
是李月娥。她不知什么时候来的,手里还拿着一根擀面杖。她冲过来,二话不说,一擀面杖就敲在了王麻子的背上。
王麻子疼得嗷嗷叫,回头看见是她,还想放几句狠话,可对上李月娥那双要喷火的眼睛,又怂了,最后骂骂咧咧地跑了。
“你没事吧?”她扔下擀面杖,赶紧扶起我,掏出手帕帮我擦脸上的土和血。
她的手帕上,有股淡淡的栀子花香。我看着她满是担忧的眼睛,心里突然就软了。
“没事,皮外伤。”我咧嘴一笑,结果扯到了嘴角的伤口,疼得直抽气。
“你真是个傻子!”她眼圈红了,“跟那种人置什么气!”
“他……他骂你!”我梗着脖子说。
她看着我,突然就不说话了,只是低着头,小心翼翼地帮我擦着伤口。
那天,我没去上工。她把我扶回家,又是给我找药,又是给我倒水。我娘看见我脸上的伤,心疼得直掉眼泪,一边骂我,一边又一个劲儿地跟李月娥道谢。
“婶,你别谢我,他……他是为了我才……”李月娥说着,脸就红了。
从那以后,村里人都知道,我王建业看上了隔壁的“豆腐西施”李月娥。闲话自然是少不了的,说我吃了熊心豹子胆,敢沾惹“扫把星”。我爹也黑着脸,把我叫到跟前,让我离她远点。
“爹,”我跪在他面前,梗着脖子说,“月娥是个好姑娘!别人不了解她,我了解!这辈子,我非她不娶!”
我爹气得拿烟袋锅敲我,被我娘给拦住了。
“老头子,”我娘叹了口气,“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主意了。我看月娥那姑娘,也是个懂事的。你就别管了。”
我跟李月娥的事,就这么半明半暗地处着。我每天照样给她家挑水,她每天照样给我留豆浆。有时候,她做豆腐忙不过来,我下了工,就会去帮她推磨。
那石磨死沉死沉的,我一个大小伙子,推几圈下来都累得满头大汗。可只要一看到她在一旁,给我递毛巾、端水的身影,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劲儿。
有一天晚上,我帮她推磨推到半夜。月光下,她小脸被豆浆的热气熏得红扑扑的,像个熟透了的苹果。
“建业,”她突然开口,“你尝尝这豆浆,看磨得够不够细。”
她舀了一勺,递到我嘴边。我心里一慌,鬼使神差地就着她的手,喝了一口。
豆浆温热,滑过喉咙,留下满口的香醇。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她看着我,突然幽幽地说了一句:“你这人,比豆浆还浓。”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手里的推杆差点脱手。我看着她,她的眼睛在月光下,亮得像两汪深潭,要把我整个人都吸进去。
“月娥……”我喉咙发干,感觉自己快要烧起来了。
她脸颊绯红,飞快地看了我一眼,又低下头,小声说:“我娘……睡着了。”
那一瞬间,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扔下手里的推杆,上前一步,一把将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。她的身子小小的,软软的,在我怀里微微颤抖。
我低头吻住了她。她的嘴唇,带着豆浆的甜香,青涩而又热烈。
……
第二天,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砖窑厂,一整天都跟踩在云彩上似的,飘飘忽忽的。逢人就傻笑,工友们都说我魔怔了。
晚上回家,我娘把我叫到跟前,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。
“建业,这是咱家祖传的银镯子,本来是留给你媳-妇的。”她把镯子塞到我手里,“明天,你拿去给月娥戴上吧。那姑娘,是个好姑娘,咱家不能亏待了人家。”
我攥着那对沉甸甸的银镯子,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
第二天,我揣着镯子,一整天都心神不宁。好不容易熬到晚上,我又去了她家。
她好像知道我要来,特意换了件新衣裳,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。
我把镯子拿出来,给她戴上。月光下,那银镯子在她皓白的手腕上,闪着柔和的光。
“月娥,”我拉着她的手,认真地说,“等我攒够了钱,我就盖三间大瓦房,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进门!”
她看着我,眼睛里含着泪,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从那以后,我干活更卖力了。除了在砖窑厂,我还揽了些私活,跟着村里的瓦匠队,四处给人盖房子。我白天在砖窑厂脱坯,晚上就去工地上砌墙。每天累得沾床就睡,可心里头,却跟揣了个小太阳似的,暖烘烘的。
一年后,我真的攒够了钱。我在我们家原来的宅基地上,盖了三间又高又亮的大瓦房,窗户都装上了那会儿时兴的玻璃。
上梁那天,按照习俗,要请全村人吃酒席。我特意把我未来丈母娘请到了上座。她看着那崭新的大瓦房,看着满院子道贺的乡亲,激动得直抹眼泪。
她拉着我的手,拍了拍我的手背,哽咽着说:“好孩子,我们家月娥……跟着你,我放心了。”
那年冬天,在一个飘着雪花的日子里,我把李月娥娶回了家。
婚礼那天,她穿着一身红棉袄,坐在我们那张新打的木床上,脸蛋红扑扑的,比我见过的任何新嫁娘都好看。
洞房花-烛夜,我给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。
她接过碗,喝了一口,抬起头,笑着看我:“建业,这豆浆,没你浓。”
我笑了,把她连人带碗一起抱进怀里。我知道,我这辈子,是离不开她这碗香醇的“豆浆”了。
婚后,我们一起经营豆腐坊,生意越做越红火。后来,我们又开了个小小的早餐店,卖豆浆,卖油条,卖豆腐脑。日子虽然辛苦,但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,吃着我们做的东西,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,我们就觉得,再累也值。
如今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。我们的小早餐店,也变成了镇上小有名气的“王记豆浆馆”。
有时候,早上磨豆浆的时候,我还会想起1989年那个春天。想起那个在石磨旁费力推磨的瘦弱姑娘,想起她递给我的第一碗豆浆,想起她在月光下对我说的那句话。
“你这人,比豆浆还浓。”
是啊,我这人,就是这么个实在的、一根筋的、浓得化不开的庄稼汉。而她,就是我这辈子,最香醇、最暖心、最离不开的那碗豆浆。
发布于:河南省东南配资-加杠杆软件-配资股网-场外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沈阳股票配资这场发生在2025年10月7日的“公益曝光”
- 下一篇: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