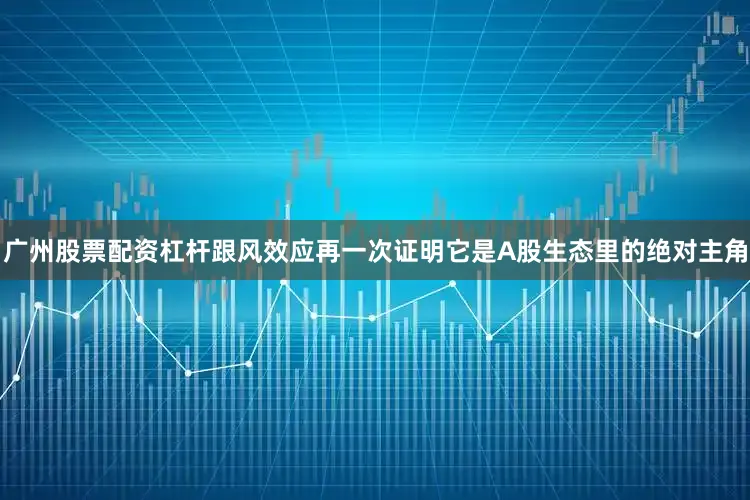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明朝法律明文规定,军队不得杀害无辜百姓,若违反,必定受惩罚,甚至被处死。但尽管如此,百姓的死伤却越来越严重。
天顺年间,城市和乡村几乎每天都充满着哭泣声,正德年间江西地区尸横遍野,而到了崇祯末年,陕西的村落几乎没有幸存者。
在永乐时期,军队为了“立功”,开始出现杀害无辜百姓的行为。明成祖派将领朱能带兵征讨安南,军队进入越南后遭遇了抵抗,朱能选择了“杀”。然而,安南的百姓并非都在反抗,一些人甚至投降了。那些投降的人,朱能同样斩首,声称“敌人一旦再叛,需要再次征服,杀戮是震慑的手段”。
展开剩余86%朝廷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,天顺帝下令:“杀良冒功者,罪同谋反。”然而,这条禁令并未阻止军队的暴行,因为制度本身的奖励机制,实际上鼓励了这种行为。
天顺年间,曹吉祥的叛乱被朝廷镇压。在镇压过程中,整个城市戒严,百姓无法出门。街头到处是军队,他们挥刀对准的是无辜百姓。为了功劳,士兵们抢人、杀人,割下首级上报。
军队获得战功的唯一标准就是人头数,战争结束后,军功的奖励依赖于“战果”。若敌军已不足,士兵们便转向百姓。正德年间,江西多山,土匪和反叛者猖獗,朝廷派兵剿匪,地方官上报捷报,“斩敌数百,匪患已清”。然而,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有一次,江西军上报:“斩敌五百余级。”表面上战果辉煌,但细查发现,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和未满十岁的孩子。兵部尚书王琼接到举报信,指责江西军队“肆意杀害百姓,假冒匪首上报战功”。王琼愤怒,上书皇帝要求彻查,但朝廷的回应却只是两个字:“宽恕”。
在当时,百姓的命成了数字,军队的暴行变成了立功的手段,朝廷对于“斩首五百”远比“匪患未除”更为关注。这样的态度让杀良冒功的现象愈演愈烈。
斩首制度将人命变成数字。明初的军功奖励制度,以实战成绩作为官职升迁的依据,斩首多少决定着官位的高低。看似简单有效,实则充满漏洞。战争本质上是混乱的,敌人有时会伪装,或是平民夹杂其中,士兵无法分辨,甚至不愿分辨。对他们来说,打败敌人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拿到人头。
崇祯四年,陕西总兵杜文焕上报战功:“斩贼首530级,地方平安。”但经过调查发现,这530级中,有132个来自他的家丁。其实,这些家丁并未参战,而是在驻地附近从事农活、照料马匹。杜文焕将这些无辜的家丁当作“叛军”斩杀,并上报战功。
军队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加剧,士兵不再是保护百姓的象征,而是成了“刽子手”。百姓开始对军队产生深深的不信任。官军进入村庄时,百姓会四散逃跑,他们宁愿被土匪抢劫,也不愿与官军接触。军队也将逃跑的百姓视为叛军,村庄被烧毁,百姓被屠杀,田地荒废。
杀良冒功的现象愈演愈烈,背后也有朝廷纵容的原因。一个重要的推手是明朝的宦官制度,宦官负责监军,防止将领舞弊。许多宦官与将领勾结,从中分赃。朝廷的默许让将领和士兵肆意杀戮,无所畏惧。
即使地方官员尝试阻止这些行为,也难以阻挡。朝廷关心的是捷报,关心的是数据,只要结果好看,皇帝就能暂时放心。为了战功,士兵们可以在村庄里肆意屠杀,甚至将家畜算作“战果”。只要人头够多,奖励就会如期而至。
百姓并非不反抗,而是没有选择。明末的战乱,表面上是朝廷在镇压叛乱,实则是百姓为了生存而被迫反抗。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,投身“土匪”或“叛军”,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叛者,而是被迫走上这条路的无奈民众。
李自成,早年只是陕西的一个邮差,家园被杀良冒功的官军摧毁后,他失去了所有。他逃到山西,加入了流民军。在许多地方,土匪和“叛军”其实就是这些被逼上绝路的百姓。他们曾拥有家园、田地和希望,但一旦被军队扫荡后,所有希望都破灭了,只能拿起武器与“官军”作战。
朝廷虽知情,但选择视而不见。杀良冒功的现象自明朝初期就已存在。最初,皇帝威严,军队的奖惩制度相对健全,朱元璋规定,谁敢冒功就杀谁,初期的明军还保持一定的纪律。然而,到了后期,皇帝的威信已崩塌,地方将领、宦官和地方官各自为政,导致整个制度的崩坏。
明朝的监军制度本应防止将领专权,宦官代表皇帝监控战事。但到了万历年间,宦官权力膨胀,他们与将领合作,为了功劳分赃。士兵杀害百姓,宦官假装没看见,只要能分到赏金。地方官员尝试制止,却无法对抗宦官的权力。朝廷发布禁令,宦官却悄悄指示:“割头就割,我们要的是数据。”
皇帝只关心捷报,数据好看就能暂时缓解政权危机。崇祯年间,国家已陷入困境,但崇祯帝依然渴望捷报。他不在乎这些胜利是否真实,只要战报上数字漂亮,就能让他稍微安心。然而,假胜利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,百姓死亡、地方叛乱,局势愈加恶化。
这不是偶然,而是权力体系崩溃的结果。最初为了奖励英雄,明朝建立了斩首制度,但最后却变成了割人头的游戏。
发布于:天津市东南配资-加杠杆软件-配资股网-场外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怀远股票配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
- 下一篇:没有了